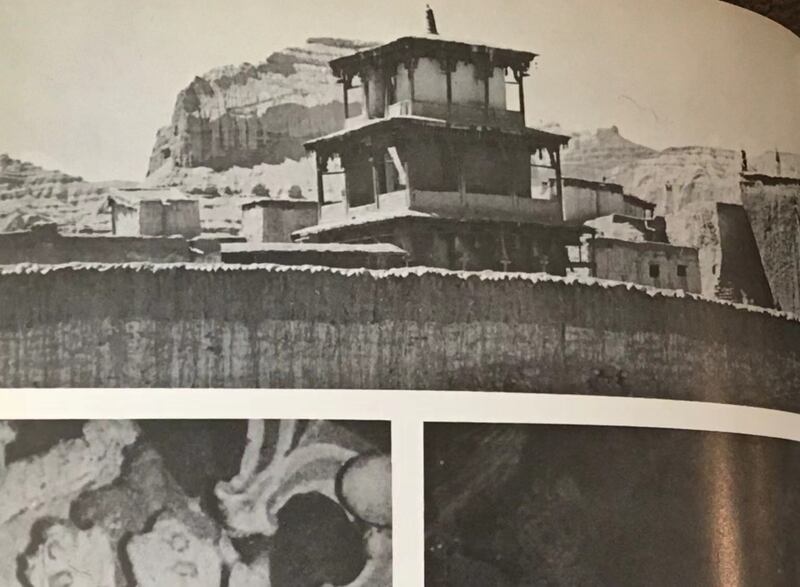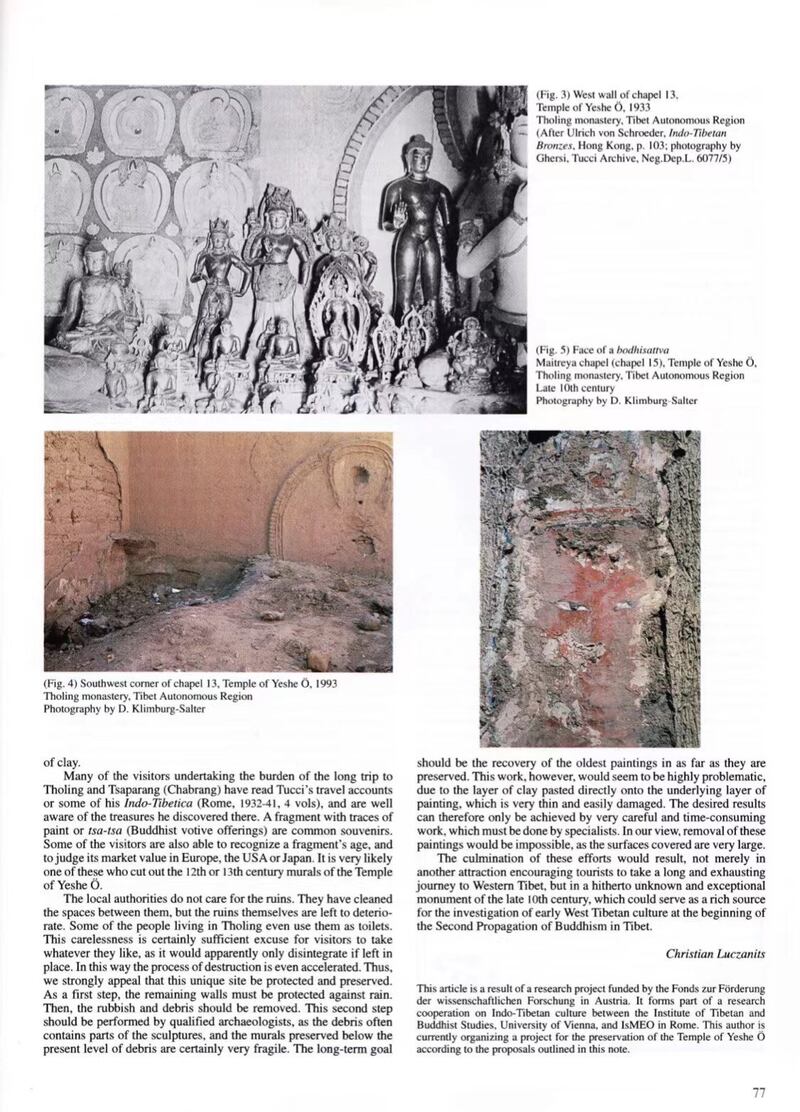4、祈愿再转圣山
我希望我用文字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佛教徒的转山朝圣,而是富有更多层次、更多意义的叙事。其中当然有政治的干预和影响,而这其实是最主要的,单纯意义上的朝圣在如今已无可能。连圣山显露真身时,朝圣者远远看见的,却是鲜红为底、黄色字体的标语牌不止一个,用中文和藏文书写政治新话,并印着中共党旗、天安门华表、大会堂的红五星天花板等。你没法不最先看见这些,突兀而醒目的色彩、文字及图示,如同不邀而至的权力者,在蓝天白云、白雪圣山、褐土绿地与经幡丛构成的本土世界中,那么地理所当然,那么地喧宾夺主。
清冷的月光也照亮了一种更深刻的关系,我认为是因果律,即业力:“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这是佛陀所言。作为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五世尊者达赖喇嘛在他的秘传中写过这行诗句:“那些因业力而觉醒的人会跳舞”!我仿佛看见,在身陷各种瘟疫的痛苦众生当中,只有因此而觉醒的人才会在月光下跳起生命的舞蹈,那是绝无仅有的美好舞蹈,既与今生难得的人身相匹配,也为来世的解脱积累着善因。
感恩诸佛菩萨、本尊护法、喇嘛上师的护佑!我当继续祈求他日获得再来转山的福报,蒙受具有永恒价值的圣山赐予加持,让我或我们再一次地,一次次地,从一场场遍布人间的瘟疫漩涡中“上来透口气”,这无疑是必须的。我还相信,类似于我在十九年前第一次转圣山,遇见了来自边界那边的行脚僧达琼喇嘛;如今第二次转圣山,遇见了来自边界这边磕长头的男女牧人。实际上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领悟了圣山本质的实修者,而我需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细细领略其中的启迪,类似于体会和呼吸不可缺少的氧气,那才是活命的气。
2021年11月写于拉萨
(本文发表于唯色RFA博客2022.05.12: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weiseblog/ws-05122022105041.html)